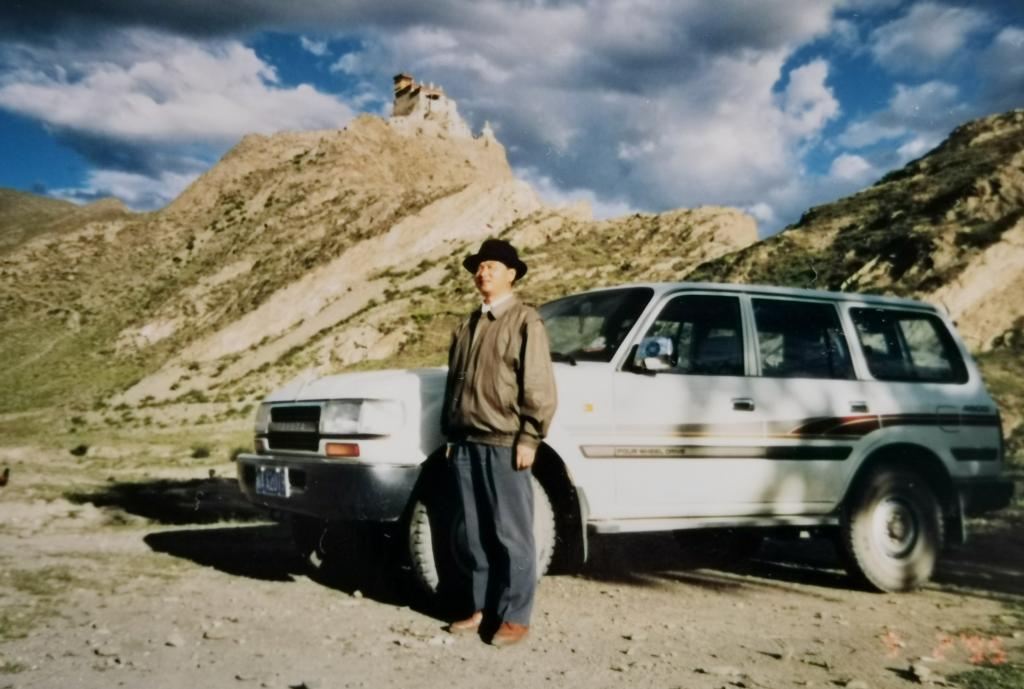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六年,我大學(xué)畢業(yè)來到西藏后���,被分到土門格拉煤礦從事機電技術(shù)工作�。這個礦在當時的西藏來說����,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企業(yè),屬自治區(qū)工業(yè)廳管轄��,但它的位置卻遠在藏北的唐古拉山腳下�����,北距長江源頭的格拉丹東雪山僅有一百多公里。礦區(qū)海拔5000多米��,北面連綿起伏的唐古拉山雪峰終年不化���,年平均溫度在攝氏零度以下����,無絕對無霜期��,含氧量還不到海平面的百分之五十�����,一年中冬季長達八個月以上����。
我一到礦上�����,礦領(lǐng)導(dǎo)就讓我負責(zé)全礦的機電技術(shù)工作���。這對剛出大學(xué)校門的我而言����,壓力之大可想而知。遇到技術(shù)上的難題�,根本找不到老師請教,甚至連參考資料都很難找到�。當時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礦上所有的發(fā)電機全部都停了,有的是柴油機壞了�����,有的是發(fā)電機出了毛病�����,有的是控制柜出了問題����。整個礦區(qū)都沒有電,晚上靠點蠟燭照明����,采掘只能停工。于是到礦上的第二天����,礦領(lǐng)導(dǎo)就要求我?guī)ьI(lǐng)其他技術(shù)人員��、工人一起盡快解決礦區(qū)供電的問題�����。我的高原反應(yīng)十分嚴重�,但看到礦領(lǐng)導(dǎo)和工人們一雙雙飽含期待的眼睛���,我堅定地接受了這個任務(wù)�����。
回到家后,我便開始翻閱一些從學(xué)校帶來的少得“可憐”的資料����,找來圖紙,開始分析計算�。第一個問題比較好解決,我發(fā)現(xiàn)柴油機和發(fā)電機沒什么大毛病��,只是由于機房的基礎(chǔ)是凍土層���,冬天的凍結(jié)和夏天的融化造成不均勻的沉降���,導(dǎo)致柴油機軸和發(fā)電機軸不同心���,法蘭盤的聯(lián)接處形成很大的剪切力,使聯(lián)接螺絲斷裂�����。我和工人師傅用一截長長的透明膠管將其中注滿清水�,做成一個簡易水平儀,測出了兩臺機器軸偏心的誤差��,后又用塞鐵仔細墊平��。三天后����,機組可以正常發(fā)電了,大家歡欣鼓舞�。后來,又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與其他技術(shù)人員��、工人一道�,把其它發(fā)電機也修好了�。第二年��,我們又將七八臺柴油發(fā)電機組集中在一起�,建了一個小型發(fā)電站。
為了解決凍土層不均勻沉降的問題���,我將廠房的基礎(chǔ)設(shè)計成一個巨大的整體性構(gòu)造�����,鋼筋混凝土的厚度足有一米�。在澆筑基礎(chǔ)的日子里���,礦上動員了大批人馬��,挑燈夜戰(zhàn)。我既任指揮也和大家一起背石子�����,拌混凝土��,干得熱火朝天��。
那是一段緊張、繁忙而又充實的日子����,除技術(shù)工作外我們還辦了職工夜校,教工人學(xué)文化�、學(xué)技術(shù),甚至還教唱歌���,組織各種有益的活動�。由于礦區(qū)的自然環(huán)境非常艱苦����,更需要互相關(guān)心和體貼,人們的感情非常淳樸自然����,藏漢族之間的關(guān)系也非常好。時至今日�����,我們與礦區(qū)工人還保持著經(jīng)常來往�����,與大家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在礦區(qū)缺氧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�����,只能慢慢適應(yīng)����。夜里的氣溫長年在零度以下,最冷的時候達零下四十多度�,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是冬季。好在礦區(qū)有煤����,每天烤火做飯的用煤都在100斤以上。但是得靠自己去煤場挑煤�,拌煤又得用土、用水�,這些都是靠自己去挖去挑。每家都用廢汽油桶做一個大爐子�,兼烤火和做飯之用,那是一只名副其實的“煤老虎”��,你每天都得不停地喂它���,然后又要把它排出的煤渣運走��,每天要為火爐耗費大量的精力���,稍有疏忽,爐子就會熄滅����,屋內(nèi)頓時變得像冰窖一樣,就會喝不上水��、吃不上飯�����。
吃菜也是礦區(qū)的一個大難題�。一年中至少有七八個月吃不上新鮮蔬菜,因為這些菜要從西藏的拉薩和青海���、甘肅甚至是新疆去采購����。由于路途遙遠��、公路顛簸,一些新鮮蔬菜還沒等運到礦區(qū)��,就成了一堆“爛泥”�。因此,在大多數(shù)情況下只好買些土豆��、蘿卜��、圓白菜���、大白菜之類�����,儲存在屋內(nèi)的菜窖里���。這些極普通的蔬菜在高原礦區(qū)都成了上等的佳肴,因為蔬菜供應(yīng)不及時��,我們很多時候�,還需靠藥片來補充維生素。
礦上的飲用水也很困難�。夏天,要用水車從河里去拉來���;冬天���,水都結(jié)成冰,只有去冰湖挖冰化水�。凍冰堅硬無比,十字鎬砸下去�����,只能砸出一點白印子來����。不過,我們知道一個訣竅��,那就是找有冰裂縫的地方去挖����,在那些地方采冰,可以大大節(jié)省勞力��。挖冰挖累了�,就躺在冰上休息一會兒;渴了����,餓了���,就吃點碎冰解渴充饑。
在礦上��,最怕的是生病��,因為嚴重缺氧��,加之其他自然條件也非常惡劣�����,即使一場小小的感冒����,也會把你折騰得掉上幾斤肉。在那段艱難的日子里��,有一件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忘懷�,那就是關(guān)于一只蘆花雞的故事。
那是一只灰白相間的小母雞�,我精心喂養(yǎng)它,看著它一天天地長大�,沒過多久它就開始下蛋�,每個月下蛋都在20多個以上��,這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簡直是個奇跡��。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�����,開始沒有在意��,還坐車到幾十公里的野外工地考察�,正好那天又刮大風(fēng)��,我們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地方步行了十多公里��。晚上回來后����,我就開始發(fā)高燒,將近四十度�。第二天上午,燒退了些����,我誰也沒有告訴�����,堅持著自己去挑煤挑水�����。到了下午��,又開始發(fā)高燒��,燒得我迷迷糊糊���,極度虛弱,連去醫(yī)院看病的力氣都沒有���,家中除了大米和開水之外�,幾乎沒有什么可吃的����。這時,我養(yǎng)的那只蘆花雞進來了�,很快地下了一個蛋,我如獲至寶��,將雞蛋撿起來,準備馬上煮著吃掉����,補充一下體能,蛋還是熱的��,我就有些不忍敲開它���。我將蛋放在桌上��,心懷一種異常的感激之情,注視著那個雞蛋�,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,當時對蘆花雞的感激與崇敬之情在我心中不斷升騰���,升騰……
當雞蛋的溫度逐漸冷卻下來后�����,我狠了狠心���,將雞蛋敲入碗中,加了一些糖����,用高壓鍋蒸熟后就吃了���。半小時后,燒竟然神奇地退下去了�,覺得有點體力,到礦區(qū)醫(yī)院拿了些藥��,兩三天后就痊愈了����!
生病那幾天,蘆花雞幾乎天天下蛋�,那是我當時擁有的最高級的食品。我下定決心����,不管多么困難,我都要把蘆花雞一直喂養(yǎng)下去����,直到有一天它自然老去。休假的時候���,我托人把它捎到拉薩喂養(yǎng)�,可惜的是,當別人又將它捎回礦區(qū)時���,它由于高原反應(yīng)而死去了�����,當我聽到這個消息��,心中涌出一陣難言的酸楚���。今天我把它記錄下來,算是對它的一種感激和記念吧�!
屈原說過:“路漫漫其修遠兮�,吾將上下而求索?����!庇腥藛栁?����,如何看待我們這批進藏的熱血青年呢�����?我始終覺得,這是一種人生的責(zé)任感與時代的使命感���。一個人既然來到這個世界��,時代就賦予你一種使命����。貢獻可以有大有小�,每個人面對的環(huán)境與條件也不一樣,但你只要盡了責(zé)任�����,你就無愧于良心���、無愧于時代�����、無愧于人生��。
【陳正榮:機電系機電專業(yè)1976屆畢業(yè)生����。】
選自《科大故事③》(2021年9月出版)(材料提供:陳正榮 整理:張瑜)

